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不会终止于亲身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当事人,也会波及到处于该环境中的重要他人(Dekel,2008)。与创伤传递相关的术语有很多,如替代创伤(vicarious tuaumatization)、二次创伤(secondary tuaumatization)、跨代创伤(cross-generational tuaumatization)等。
侧重于代际之间,特别是从父母到子女的传递过程,曾被形容为跨代(trans-generational/cross-generational)传递、代际间(inter-generational)传递或多代(multi-generational)传递(Kellermann,2001a)。本文中的“代际传递”(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ITT)侧重于创伤的影响在亲属关系中自上而下的传递,不仅包括亲子之间的直接传递也包括多代之间的隔代传递。
以“trauma”、“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holocaust trauma”等搜索词检索文献,发现关于创伤代际传递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广义的创伤,即广泛性的创伤性事件,不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如抑郁(Garber,2010)、攻击和反社会性行为(Tzoumakis,2012)、虐待(Lev-Wiesel,2006)、犯罪及物质滥用(Whiting,2009)等,这一类创伤具有普遍性。另一类是基于狭义的创伤,即特定的创伤性事件,特别是集体性的重大创伤性事件,如大屠杀、战争、恐怖事件等。这两类创伤并不能截然区分,第二类创伤的代际传递具体到每个家庭通常表现为第一类创伤传递的形式,如通过养育方式(Kitamura,2009)、依恋类型(Miljkovitch,2012)、沟通方式(Giladi,2012)等进行传递。本文主要以集体性创伤性事件为主,尤以大屠杀为例,探讨创伤自上而下的代际传递。
研究现状分析
对创伤代际传递现象的研究本身存在很大争论,总体研究结论迥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结论不一致。大量的临床资料显示创伤存在代际传递的现象,而研究者却无法用客观可靠的测量工具证实这一点(Kellermann,2001a)。临床工作者通过观察、临床实践和质性研究的方法,报告创伤者的后代具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如创伤代际传递的内容及机制都是基于对个案访谈资料的分析(Kellermann,2001a)。对于实验研究,Kellerman(2000)对1973-1999年间的35个对照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显示创伤者后代的患病率并没有比控制组高,除非创伤者后代面临生命威胁的情境(Van Ijzendoorn,2005)。不过,也有研究采用自评问卷的方法发现,在689个一战经历者的后代中,有三分之一(35%)的后代表现出PTSD的临床症状(Karenian,2011)。不同研究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差异,目前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释。
二是临床样本和非临床样本结论不一致。Van Ijzendoorn等人(2005)对32个样本,4418个参与者进行了元分析,发现在临床样本中大屠杀幸存者子女的适应性功能与对照组差异显著,在非临床样本中大屠杀幸存者子女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即创伤的代际传递只发生在临床样本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大屠杀幸存者对孙辈的影响,也再次得出了同样的矛盾结论。Sagi-Schwartz等(2008)对13个非临床样本,共1012个被试进行元分析显示,创伤者后代没有比对照组表现出更多的临床症状。对于非临床样本没有表现出创伤的代际传递,不管是直接传递还是隔代传递,研究者多采用Paris(2000)的生物心理-痛苦模型来解释,即认为是否产生症状以及症状的具体形式取决于创伤后的社会支持。
研究结论不一致,有可能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差异。实验研究对于创伤者的判定主要是基于参与战争与否,或患有PTSD与否,并没有考虑到未参与战争和未患PTSD但同样也受到了创伤性事件影响的事实。其次,量化的测量工具,特别是临床所用的筛查工具,多是创伤性影响到达一定程度才被认为是创伤者,非临床样本中也有很多人经受创伤的影响但未获得临床诊断的认可。再次,创伤代际传递的研究者多着眼于创伤的消极影响,也有很大部分的创伤者后代适应良好,没有表现出临床症状和功能损坏,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未受到祖父辈创伤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第三代及之后的后代而言,创伤代际传递的内容及方式可能发生了变化,创伤也可以赋予他们积极的力量。
影响创伤代际传递的因素
创伤的代际传递主要是环境与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Rhee和Waldman(2002)对51对同卵双生子和寄养子女进行的研究,以及Tuvblad等(2011)对2600对同卵双生子进行的研究发现,基因因素在反社会行为的代际传递中占41%和61%的比率。同时,环境也起着重要的作用。Rosenthal(2011)发现在同是大屠杀幸存者孩子的同胞身上存在着特定的倾向,他们都具有更多的人际问题和更低的自尊。尽管如此,也并不是所有创伤者的后代都以同样的形式同等程度地受到父母创伤的影响。创伤的代际传递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个体差异性,这主要体现在父母、个体自身和社会环境因素等方面的易感性上。这些因素既可以直接影响创伤的代际传递,也可以作为中介变量产生影响(Testa,2011)。
在父母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父母的创伤程度和患病人数。Davidson和Mellor(2001)对比了3组孩子的家庭功能情况。3组孩子分别是父亲参与战争并患有PTSD,父亲参与战争但没患PTSD,父亲没有参与战争,结果显示父亲参与战争并患有PTSD的孩子家庭功能最差。这也说明代际传递来源于PTSD而非参与战争。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父亲的情况,母亲对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鲜有研究,这可能与男性是战争的主力有关。另外,Van Ijzendoorn等人(2005)的元分析显示,在双亲(比起单亲)都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身上,创伤的代际传递更容易发生。尽管很少有研究能够明确表明父母创伤程度对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而且有研究显示父母患PTSD的严重程度与孩子问题行为的严重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有研究显示,相比于PTSD的严重程度,PTSD的后果(如家庭暴力)是孩子痛苦水平更好的预测指标(Harkness,1993)。
在孩子方面,Rosenthal(2011)、Dekel和Goldblatt(2008)探讨了孩子的性别、年龄、出生次序和父亲受到创伤的时间对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关于孩子性别影响的研究比较少,并且结论不一,有两篇文献显示父亲-儿子和父亲-女儿关系中,男孩、女孩报告的痛苦水平有差别(Harkness,1993;Parsons,1990),一篇文献显示创伤的代际传递没有性别差别(Dansby,1999),并且这些研究都仅限于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关于年龄,Dekel和Goldblatt(2008)发现大部分研究的孩子都是在14岁以上,并且极少有研究对孩子的年龄进行控制,这就导致很难区分孩子的痛苦是由父亲的创伤传递而来还是与特定年龄段(如青春期)的特征有关。另外,Rosenthal(2011)通过对大屠杀幸存者孩子的同胞进行研究,发现更年长的同胞具有更高的创伤代际传递易感性,原因可能是他们承担更多的职责,或者是出生于离战争结束更近的时期。但如果是在父母创伤事件之前出生的孩子,那可能会因为有部分健康生活的经历而能减缓创伤的代际传递(Dekel,2008)。
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Paris(2000)在其生物心理-痛苦模型中认为,创伤后的社会支持能够影响创伤症状的基线,并且还可能决定症状的具体形式。从大的社会环境来说,以犹太人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幸存者被认为是纳粹政府的被动受害者,幸存者们倾向于忘记或者压抑他们的遭遇。从小的社会环境来说,若幸存者后代有离家的经历(如上学、参加青年运动或夏令营),与父母的距离能使得他们更好地区分父母与他们自己。在家庭环境中,家庭如果加入幸存者组织,在家庭中能够以不恐怖的方式公开讲述受难的经历,那创伤代际传递的负面影响要小于封闭的、对灾难保持沉默的家庭(Wiseman,2006)。
创伤传递的内容
从传统意义来说,创伤主要产生消极的影响和后果,但我们发现创伤者的后代并非以同样的方式来表现创伤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创伤代际传递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症状的传递及其表现
从心理健康方面来看,症状的传递构成创伤代际传递的主要内容。症状包括认知和情感两方面。认知层面包括对灾难的预期,对灾难重演的恐惧,死亡侵袭感和对灾难经验的替代性分享(Kellerman,2001a)。在认知功能上主要表现为记忆力受损,注意力偏差,刻板和负面歪曲的认知,这些认知干扰将导致高级认知功能的抑制,防御性行为以及紊乱的情感(如抑郁、焦虑)(Kaitz,2009)。在情感方面主要表现为毁灭性焦虑,迫害性梦魇,与丧失和哀悼相关的躁狂心境,面对未解决冲突的愧疚和愤怒(Kellerman,2001a)。
与症状高度相关的是人际功能,包括家庭功能。创伤者后代的人际缺陷主要体现为过度重视家庭中的依恋关系和对家庭的依赖性,并夸大建立亲密关系和解决人际冲突的困难(Kellerman,2001a)。Harkness(1993)发现,老兵们的教养方式以控制、过度保护和苛刻为特征,而安全依恋关系的建立需要独立且对孩子的需求敏感的照料者,任何形式的情感淡漠、分离和回避以及过度保护都将直接损害依恋关系的建立。并且,父母应对创伤的防御方式也会传递到孩子身上,创伤者后代可能更多地采取回避、压抑、隔离的行为方式。
另外,在创伤的具体传递过程中,卷入其中的每一代人有各自不同的症状和表现。Kahane-Nissenbaum(2011)纵向探讨了大屠杀在三代人身上的不同症状和影响。他指出第一代创伤者主要表现为患有PTSD,有更多的睡眠障碍、抑郁和分离症状,并且普遍以失语和记忆力损伤为防御方式。创伤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长期的涉及情感、生理、社交等各方面的损害。对于第二代创伤者来说,他们对PTSD的易感性比常人更高,应对创伤影响的方式更加复杂。一方面,为了保护父母不受到更多的伤害,他们必须压抑自己的愤怒,忍受来自父母的“幸存者内疚”,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同时还必须照顾好父母,并且还要补偿父母因为自身受损而未能满足的不现实的期望。另一方面,父母的过度保护和依赖使得他们无法独立。并且,第二代创伤者还可能需要应对移民带来的压力,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并帮助父母适应新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为“父母的父母”。所以对他们来说,创伤的影响意味着负重累累,既要忍受内疚,压抑愤怒,还要照顾父母,承担压力和期望。第三代依旧很重要并且有其特殊意义,因为一般来说第三代是和原初创伤者现实接触的最后一代。Kahane-Nissenbaum(2011)根据Viktor Frank存在意义理论设计的实验结果显示,第三代创伤者更多地将祖辈的创伤经历视为宝贵“遗产”和力量的源泉,视祖辈为英雄而非受害者,对祖辈幸存的能力持有敬畏之心。他们显著的特征是对灾难制造者以及否认灾难发生的愤怒,也包括对自己未能在祖辈有生之年与之交流和询问的悔恨,他们自觉拥有保存和传承这份历史的职责,并且具有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使命感。并且,第三代创伤者更加珍视与身边人的关系,对祖父辈赋予的生命和生活充满感恩珍惜之情。
(二)任务的传递及其应对
从家庭层面来看,创伤的代际传递是任务的传递。幸存者后代接收到的家族任务不同,对创伤的应对方式不同。比较典型的任务有以下几种:其一,修复父母。自觉承担这个任务的孩子将父母视为生命的全部,成为父母情绪情感的储存器,被迫处理父母无法消化的羞耻感、暴怒、无助和内疚等情绪(Fromm,2006),束缚在父母身边无法分化。其二,雪耻复仇。无论是大屠杀还是其他集体性创伤,“受害者”的身份都蕴含着深切的耻辱与愤怒。亲历创伤性事件的受害者们大都忍气吞声,自轻自贱,苟且偷生。他们或者暴怒或者缄口沉默,耻辱、怨恨和无助的气息弥漫着整个家庭,诱使着他们的后代替为表达或者改变。其三,充当替代品,包括充当去世者和存活者的替代品。前者主要是替代儿童,他们的任务就是延续某人的生命,不断地填补家人甚至整个民族的空虚(Kogan,2003)。“在这种传递中,父母或其他重要个体将来自于年长个体心理的预先设计的自我或客体表征,寄存在一个孩子发展中的自我表征上”(Volkan,1997)。存活者的替代品是指不断地满足幸存者尚未完成的愿望,肩负着沉重的期望与压力。其四,弥补重大的损失。幸存者常会觉得是自己没能阻止或造成了灾难的发生,这一方面与幸存者内疚(survival guilt)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过度补偿行为。如幸存者后代常见于社会工作者、身心疾病治疗者、育人工作者、律师等助人职业中(Wardi,1992)。其五,保存历史、诉诸于众。一些幸存者后代致力于追寻家庭的记忆,或投身于创伤事件的资料收集、出版发表工作中,具有保存家庭、民族历史的使命。
(三)身份的混乱及其后果
再次,从个体层面来看,创伤的传递是身份的传递。受父母创伤影响的孩子过度认同父母的受害者角色,对父母的损失进行过度补偿,甚至成为逝者的替代品(Kogan,2003),这些都导致自我界限的缺失和模糊,以致孩子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在波兰的大屠杀幸存者将他们的犹太人身份换成更为安全的天主教徒和波兰人身份。但是当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的后代,发现他们的父母是犹太人时,他们突然面临着一种窘境(Muller-Paisner,2002)。首先,犹太人身份带来耻辱。他们面临着去尝试理解家族遭遇大屠杀的恐惧,尝试去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与经验。其次,身份感遭到损坏。天主教与犹太教双重身份的矛盾和分裂,使得他们的身份感及自我认同感遭到破坏甚至丧失。再次,与父母及亲人的关系遭到破坏。无论选择和亲属相同的身份,还是划清界限另择身份,都使得亲属间的情感联结受到严重的威胁。即使有部分幸存者后代接纳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追寻家庭的历史,但他们的父母未必愿意承认和回忆他们的犹太人生活,更不用说允许他们的孩子回归犹太人身份(Muller-Paisner,2002)。
四、创伤代际传递的解释模型
在与父母相处过程中,通过父母受到创伤影响的具体生活细节,后代可以感受到创伤的传递,如体貌特征,父母向后代讲述受难过程中留下的疤痕;在后代人身上看到灾难中丧生亲人的身体特征,如蓝眼睛(Fromm,2006);在后代人身上回忆起战争中的经历,如条纹衣服、马丁靴(Kellermann,2001a);听到后代唱起某首特殊意义的歌(Fromm,2006);或者幸存者看着后代的眼神、无言的眼泪和半夜的尖叫以及和去世的亲人一样的名字等等,这些都足以勾起幸存者对创伤的回忆,激起他们各式各样的反应。而作为后代,也会慢慢在父辈的反应中习得家庭的某些规则和行为方式,意识到一些异样和秘密的存在。
(一)创伤的消极影响
Kellermann(2001a)着眼于创伤的消极影响,探讨了创伤代际传递的深层机制,提出心理动力模型、社会文化模型、家庭系统模型和生物模型。之后,Sotero(2006)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历史性创伤的模型。
心理动力关系模型认为创伤通过人际关系,传递了无意识中被置换了的情感。精神分析强调创伤通过无意识的认同过程进行传递,是自体和客体分化失败的结果。即原初创伤者无法在意识层面表达的情感传递到后代身上,被后代无意识接收,并以各种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完成一个“投射性认同”的过程。
社会文化模型认为创伤通过社会化过程传递了养育模式和社会角色。文化方面体现在社会规范和信仰对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如社会倾向于将战争或强奸等带来的创伤视为被动受害或者羞辱。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孩子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来学习,强调孩子如何通过父母的养育行为来形成自己的意象。父母的拒绝、过度保护、过度纵容或严厉,或者前后不一致被认为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因素。另外,依恋理论也与父母的教养行为密切相关。安全的依恋关系需要父母稳定和敏感的照顾,受创伤影响的父母因自身的不稳定无法提供给孩子安全的依恋模式(Weingarten,2004),从而造成养育的创伤。
家庭系统模型认为创伤通过沟通传递了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缠绕和羁绊的关系。创伤家庭的外部联系经常局限于他们自身或者和他们有相似经历的人群。在封闭且狭小的交际圈内,父母和孩子经常替代性认同,父母通过孩子存活,孩子体验父母的创伤,边界模糊混乱,以致父母无意识拴住孩子。孩子既愤怒又内疚地照顾父母,甚至父母和孩子的角色发生互换。而这些都发生在无意识层面,通过非言语的、模糊的、内疚导向的沟通方式一唱一和。过度的沉默导致很多创伤者后代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和父母交往时的感受,而只是“难以名状的悲伤和恐惧”。同时,沉默也意味着否定和冷漠,将引导孩子形成怯懦和退缩的行为方式。另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是过度公开与创伤相关的细节,并且缺乏正确的引导(Sagi-Schwartz,2008)。特别是年幼的孩子无法消化大量的负面信息并且会通过想象夸大事情的恐怖性。另外,家庭氛围,如持续的家庭暴力会产生长期的消极影响(Sagi-Schwartz,2008);家庭角色的缺席,包括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缺席;家庭角色不稳定,如父母突然变得回避冷漠或易激惹暴怒,让孩子丧失对父母角色的一致性,变得不知所措或者归咎于自己;家庭结构不稳定,父母关系因创伤事件的影响而糟糕或破裂,都会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造成不良影响(Kelly,2011)。
生物模型认为创伤通过基因传递了对PTSD的遗传易感性。生物模型假定创伤的代际传递中是基因或遗传素质被传递给了后代,就像遗传性疾病一样。它假定基因具有记忆代码,记忆代码通过大脑的电传递或化学传递传达给后代。Yehuda(2002)发现相比对照组,双亲都患有PTSD的孩子其皮质醇水平最低。并且,研究者也发现PTSD的促发(Kilpatrick,2007)、与虐待相关的抑郁(Kaufman,2006)和痛苦的生活事件(Caspi,2003)都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创伤的积极意义
以上模型都是针对创伤的病理特征而进行的解释,其后Kahane-Nissenbaum(2011)引入Viktor Frank的存在意义理论,从积极的角度出发,寻求创伤代际传递对个人和人类的意义。
存在意义理论认为人主要关心的并不是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了解生命的意义,明白为何而活(维克多,1998)。Frank亲身经历集中营磨难之后提出意义治疗法,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一个人不能寻求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职和使命,需要具体地去实现,“能够负责”是人类存在最主要的本质。意义有3个来源:通过创造和工作,通过某种经历感受或与某人相遇相爱,通过对不可避免的苦难所采取的态度。当一个人面临无可改变的厄运,创造性价值和体验的价值都难于实现时,他也得到了一个机会,去实现最深的意义与最高的价值——态度的价值。当然,只有在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忍受痛苦才具有巨大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发现一种受难的意义时,受难就不再是受难了。可见,存在意义理论更少地回溯过去对现在的影响,也不以代际联系为中心,而将目光朝向未来,指向意义的追寻,更多地重视创伤代际传递有可能的积极作用,这给创伤代际传递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视角。
五、创伤代际传递的诊断与治疗
(一)创伤代际传递的诊断
现今临床上最常用的创伤诊断工具是DSM-Ⅳ,其中有关PTSD诊断标准已被广泛接受,但PTSD诊断项目并不能区别出不同程度的创伤,为更准确地反映出创伤症状在代际间的传递,Kellermann(1999)专门针对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提出了“大屠杀幸存者症状”(holocaust survivor syndrome)、“儿童幸存者症状”(child survivor syndrome)和“第二代症状”(second generation syndrome)的概念。其中,“大屠杀幸存者”是指经历大屠杀时已经成年的幸存者,“儿童幸存者”是指经历大屠杀时年龄未满16岁的幸存者,“第二代”即是指前两类幸存者的子女,也称“幸存者的孩子”。
整体来说,这些对象对于大屠杀事件的反应方式是有差异的,临床诊断的侧重点也所不同。对于当时已成年的大屠杀幸存者来说,抑郁是一个典型的特征,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更适宜对这一类人群的诊断。儿童幸存者的症状虽然也有很多表现形式,但整体上更倾向于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并根据创伤的年龄常伴有不同程度的人格障碍。而幸存者的第二代,一方面会被神经症性的冲突和认同问题带来的焦虑所折磨,另一方面也会因为社交和职业功能的受损而被认为具有人格障碍。另外,也因为第二代的父母大多数缺乏养育经验,子女多数存在发展缺陷以及分离个体化失败,所以他们对环境及自身持有僵硬的、适应不良的认知模式,也因此Kellermann(1999)认为需要一个新的诊断类别——“创伤传递综合征”(transmitted trauma syndrome)。
(二)创伤代际传递的治疗
代际创伤的治疗与其他创伤的治疗并无根本的区别,只是代际创伤的治疗更强调创伤“一脉相承”的特点,把个体的历史放到所处环境的历史当中去理解,并试图整合。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精神分析取向治疗、认知行为治疗、行为取向治疗及辩证行为疗法(DBT)都是很有效的治疗方法(Goldsmith,2004)。大体上来说,基于传统家庭或婚姻治疗模型的系统性治疗(systemic treatments)致力于缓解症状,减少创伤引起的压力,支持性治疗(support treatments)侧重于改善关系,增加社会支持(Galovski,2004)。除此之外,代际创伤的治疗更要求历史背景与现实情况的结合,个人境遇与社会环境的结合。如Goldsmith等(2004)认为,对于创伤幸存者的治疗来说,对创伤性经历的意识水平是治疗有效性的关键,这不仅是个人层面上意识到创伤性经历的存在及其影响,还有专业学科以及整个社会对创伤的意识水平和承认程度。
很少有人对创伤者及其后代进行代际之间的联系同时又加以区分,至今还没有专门针对代际创伤的治疗。Kellermann(2001b)根据自己在AMCHA(以色列的一个心理援助中心)的经历,将来访者的症状与家庭经历的创伤结合起来理解,并强调代际之间的差异,总结出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各自的特点及更适合的治疗方式。
对大屠杀幸存者来说,最为迫切的是症状的缓解。对于大屠杀的经历和痛苦的记忆,他们试图压抑、否认并忘记,所以创伤性经历得到承认、言说和情感表达是治疗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保持记忆要好于试图否认和遗忘。提供希望和安全、信任的关系,让他们能够进行充分的哀悼是很重要的。
对儿童幸存者来说,他们在更小的年龄经历了大屠杀,经受的损伤更大(Fridman,2011),治疗也更加棘手。对于他们来说,治疗的重点在于尽快恢复情感的平衡和功能的完整。如,巩固现有的防御和应对机制,预防潜在应激源的影响,增强自我的力量,使得他们能够面对被抛弃、被亲人暴力折磨的悲痛经历。并且在咨询师充当好母亲的抱持性关系中,他们可以通过替代认同习得好的情感体验,增强应对丧失的能力,并对生活和认同的来源持有新的视角。对于当时年幼的他们来说,很多痛苦的经历尚未到达言语表达的水平,所以像艺术、创造性书写、音乐或者舞动疗法等表达治疗可能更易于情感的表达。
对于幸存者的孩子来说,创伤代际传递的概念尤为重要。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模糊地意识到父辈的创伤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表达看起来毫无根据的愤怒、焦虑和抑郁等情绪。也因此,幸存者的孩子的治疗多集中在鼓励情感和想法的自由表达上。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能够使他们更多地意识到无意识或者前意识的内容。团体治疗也能让来访者相互交流和比较各自的经历,进而使他们更接纳自己,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第二代”身份认同。这些治疗都有助于他们找到问题的根源,并进行逐步的整合。另外,很多第二代孩子的问题都集中在与父母关系的纠葛上,治疗的重要任务是帮助孩子与父母分离,获得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
六、研究的问题与启示
创伤的代际传递研究的问题比较多集中于研究方法上。大多数的研究是质性研究,即采取的是个案研究的方式,研究结论基于临床工作的观察和发现,很少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实证研究多采取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范式,获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依然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在组别的设置上,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采取创伤组和非创伤组两组对照,只有极少数的研究设置了三个组,对创伤的代际传递是由于患PTSD的影响,还是参与战争的影响进行了区分(Davidson,2001)。在样本的选择上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差。对于元分析来说,几乎所有的元分析都排除了个案研究的文献,并且对入选的实证研究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得出来的元分析结果只是基于部分的研究,并不完全具有代表性。对于具体的实证研究来说,被试的抽取可能是通过一次会谈或者是治疗项目,这些被试本身就具有临床症状,在他们身上来测量创伤的代际传递可能说服力不够,这也很有可能是临床资料支持创伤代际传递现象存在的原因之一。另外,研究者逐步意识到在施测方法上要更加重视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的结合。传统的测量养育行为的工具可能并不能反映新情境下的养育方式(Kellermann,2001a),对于重大创伤等非平常性事件,自我报告、半结构访谈、讲故事等质性研究的方式可能更加适合。再者,现有的实证研究很少涉及母亲的创伤对孩子的影响(Cort,2011),但是母亲对于亲密关系和依恋模式的建立非常重要(Belt,2012)。
值得关注的是,“代际传递”的说法本身侧重于祖父辈作为施与方的主导性,而轻视了后代作为承受方的自主性。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创伤者的后代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并不是所有创伤者的后代都被卷入了祖父辈创伤的漩涡。对于祖父辈的创伤性影响,后代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自主性来选择承接什么,承接多少,以及以何种方式承接,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在这个意义上,“代际传承”的说法可能更兼顾祖父辈和后代双方的自主性。同时,创伤代际传递的研究过少地关注其积极方面。创伤者的后代可能获得了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Tedeschi,1996),在与创伤性事件或情境进行抗争后体验到了心理方面的正性变化,如习得了父母成功应对创伤的方式,变得更加独立自主,幽默智慧等等。但是几乎没有研究把注意力放在祖父辈经历了创伤但依旧适应良好的孩子身上,他们身上可能具有的资源也许正是打破创伤代际传递的突破口。并且,创伤后成长概念的提出一改心理病理领域一直以缺陷为基础的研究预设,强调创伤后个体自我恢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涂阳军,2010),也为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积极的视角。
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何国内关于创伤代际传递的研究如此缺乏。国内关于创伤代际传递的研究仅限于攻击(刘莉,2011)、体罚(邢晓沛,2011)、依恋模式(陈琳,2005)等狭小的领域,而缺乏对我国集体性创伤代际传递的心理学研究。作者之所以对集体性创伤进行强调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集体性创伤波及的范围大,影响深。其次,集体性创伤,特别是应对集体性创伤的方式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国民性和文化,而所属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对心理健康水平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中国的孝道是否与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密切关系,中国的亲子位置是否和西方有所不同,权利和负债又是如何,这都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徐汉明,2010)。事实上,我们存在太多的集体性创伤,如南京大屠杀、唐山大地震及文化大革命等。这些集体性创伤已经分别经历了许多代人,必然存在创伤代际传递的事实,值得深入研究。以文化大革命为例,国内有很多关于文革的述评、回忆录、概论、评议类文章但缺乏系统的研究,并且大部分集中在政治、经济及文学等方面。虽然也开始有研究者对文革进行心理学研究,如关于精神创伤(俞佩淋,2011)、集体记忆(艾娟,2010)的研究,但缺乏具体探讨文革对民众心理健康影响及代际创伤治疗的研究。希望通过对创伤代际传递概念的引入,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借鉴,有助于我们自身尝试着去认识我们的集体性创伤以及创伤的代际传递。
综上所述,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不会终止于亲身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当事人,也会波及当事人的后代。以往的研究从父母、孩子和环境等方面探讨了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发现创伤的传递主要表现为症状、任务以及身份的传递,并从心理动力学、社会文化、家庭系统、生理机制及存在意义理论方面解释了创伤代际传递的机制。未来研究应更重视创伤传递过程中不同代之间在表现形式、诊断和治疗上的差异,关注代际创伤的积极意义,并重视国内集体性创伤的代际传递。
参考文献
[1]艾娟.知青集体记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0.
[2]陈琳,桑标.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性.心理科学进展,2005,13(3):267-275.
[3]刘莉,王美芳,邢晓沛.父母心理攻击:代际传递与配偶对代际传递的调节作用.心理科学进展,2011,19(3):328-335.
[4]涂阳军,郭永玉.创伤后成长:概念、影响因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心理科学进展,2010,18(1):114-122.
[5]维克多•弗兰克.活出意义来.上海:三联书店,1998.
[6]邢晓沛,张燕翎,王美芳.父母体罚的代际传递:体罚态度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6):827-829.
[7]徐汉明,盛晓春.家庭治疗: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8]俞佩淋.作为症候的“文革”记忆书写.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1.
[9]Belt R H,Kouvo A,Flykt M,et al.Intercept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cycle of maternal trauma and loss through mother-infant psychotherapy:A case study using attachment-derived methods.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2012,18(1):100-120.
[10]Caspi A,Sugden K,Moffitt T E,et al.Influence of life stress on depression:Moderation by a polymorphism in the 5-HTT gene.Science,2003,301(5631):386-389.
[11]Cort NA,Toth SL,Cerulli C,et al.Maternal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hildhood multitypemaltreatment.Journal of Aggression,Maltreatment & Trauma,2011,20(1):20-39.
[12]Dansby VS,MarinelliRP.Adolescent children of Vietnam combat veteran fathers:A population at risk.Journal of Adolescence,1999,22(3):329-340.
[13]Davidson AC,Mellor DJ.The adjustment of children of Australian Vietnam veterans:Is there evidence for 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effects of war-related traum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2001,35(3):345-351.
[14]Dekel R,Goldblatt H.Is ther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The case of combat veteranschildren.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2008,78(3):281-289.
[15]Fridman A,Bakermans-Kranenburg MJ,Sagi-Schwartz A,et al.Coping in old age with extreme childhood trauma:Aging Holocaust survivors and their offspring facing new challenges.Aging& Mental Health,2011,15(2):232-242.
[16]Fromm MG.A view from riggs:Treatment resistance and patient authority.I.Transmission of trauma and treatment resistanc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 and Dynamic Psychiatry,2006,34(3):445-459.
[17]Galovski T,Lyons JA.Psychologicalsequelae of combat violence:A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PTSD on the veterans family and possible interventions.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2004,9(5):477-501.
[18]Garber J,Cole DA.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epression:A launch and grow model of change across adolescence.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2010,22(4):819-830.
[19]Giladi L,Bell TS.Protective Factors for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Among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 Holocaust Survivors.PsychologicalTrauma:Theory,Research,Practice,and Policy,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2012.
[20]Goldsmith RE,Barlow MR,FreydJJ.Knowing and not knowing about trauma:Implications for therapy.Psychotherapy:Theory,Research,Practice,Training,2004,41(4):448-463.
[21]HarknessLL.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war-related trauma //Wilson JP ,Raphael B.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s.NewYork:Plenum Press,1993:635-643.
[22]Kahane-NissenbaumMC.Exploring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n third generation Holocautsurvivors.Unpublisheddoctori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olarly Commons,2011.
[23]Kaitz M,Levy M,Ebstein R,et al.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trauma from terror:A real possibility.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2009,30(2):158-179.
[24]Karenian H,Livaditis M,Karenian S,et al.Collective trauma transmission and traumatic reactions among descendants of Armenian refuge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2011,57(4):327-337.
[25]Kaufman J,Yang BZ,Douglas-Palumberi H,et al.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5-HTTLPR gene intera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modifiers of depression in children.Biological Psychiatry,2006,59(8):673-680.
[26]KellermannNPF.Diagnosis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nd their children.Israel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Related Sciences,1999,36:55-64.
[27] Kellerman NPF.Psychopathology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Israel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Related Sciences,2000,38(1):36-46.
[28]KellermannNPF.Transmission of Holocaust trauma-An integrative view.Psychiatry:Interperson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2001a,64(3):256-267.
[29]KellermannNPF.The long-term psychological effects and treatment of Holocaust trauma.Journal of Loss &Trauma,2001b,6(3):197-218.
[30]Kelly KV.Bereavement,doubt,and the loved body:A 9/11 meditation.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2011,50(3):516-520.
[31]Kilpatrick DG.,Koenen KC,Ruggiero KJ,et al.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otype and social support and moderatio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depression in hurricane-exposed adults.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2007,164(11):1693-1699.
[32]Kitamura T,Shikai N,Uji M,et al.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arenting style and personality:Direct Influence or Mediation.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2009,18(5):541-556.
[33]KoganI.On being a dead,beloved child.Psychoanalytic Quarterly,2003,72(3):727-766.
[34]Lev-Wiesel R.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exual abuse.Motherhood in the shadow of incest.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2006,15(2):75-101.
[35]Miljkovitch R,Danet M,Bernier A.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single parenthood in France.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2012,26(5):784-792.
[36]Muller-PaisnerV.Poland:Crises in Christian-Jewish identity.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analytic Studies,2002,4(1):13-30.
[37]Paris J.Predispositions,personality traits,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Harvard Review of Psychiatry,2000,8(4):175-183.
[38]Parsons J,Kehle TJ,Owen SV.Incidence of behavior problems among children of Vietnam war veterans.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1990,11(4):253-259.
[39]Rhee SH,Waldman ID.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antisocial behavior:Ameta-analysis of twin and adoption studies.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2,128(3):490-529.
[40]Rosenthal J.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Chicago:The Chicago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2011.
[41]Sagi-Schwartz A,van IJzendoorn MH,Bakermans- KranenburgMJ.Doe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skip a generation? No meta-analytic evidence for tertiary traumatization with third generation of Holocaust survivors.Attachment& Human Development,2008,10(2):105-121.
[42]Sotero M.A conceptual model of historical trauma:Implications for public health practice and research.Journal of Health Disparities Research and Practice,2006,1(1):93-108.
[43]Tedeschi RG.,Calhoun LG.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Measuring the positive legacy of trauma.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1996,9(3):455-471.
[44]Testa M,Hoffman JH,Livingston JA.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exual victimization vulnerability as mediated via parenting.Child Abuse & Neglect,2011,35(5):363-371.
[45]Tuvblad C,Narusyte J,Grann M,et al.The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etiology of antisocial behavior from childhood to emerging adulthood.Behavior Genetics,2011,41(5):629-640.
[46]Tzoumakis S,Lussier P,CorradoR.Female juvenile delinquency,motherhood,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ggress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r.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2012,30(2):211-237.
[47]Van Ijzendoorn MH,BakermansKranenburg MJ,Sagi Schwartz A.Are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less well adapted? A meta 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secondary traumatization.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2005,16(5):459-469.
[48]Volkan VD,AstG.Siblings in the Unconscious and Psychopathology:Womb Fantasies,Claustrophobias,Fear of Pregnancy,Murderous Rage,Animal Symbolism,Christmas and Easter Neuroses,and Twinnings or Identifications with Sisters and Brothers.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97.
[49]Wardi D,GoldblumNT.Memorialcandles: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NewYork:Tavistock/Routledge,1992.
[50]Weingarten K.Witnessing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families:Mechanism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clinical interventions.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2004,30(1):45-59.
[51]Whiting JB,Simmons LA,Havens JR,et al.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violence:The influence of self-appraisals,mental disorders and substance abuse.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2009,24(8):639-648.
[52]Wiseman H,Metzl E,Barber JP.Anger,guilt,and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rauma in the interpersonal narratives of second generation Holocaust survivors.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2006,76(2):176-184.
[53]Yehuda R,Halligan SL,BiererLM.Cortisol levels in adult offspring of Holocaust survivors:Relation to PTSD symptom severity in the parent and child.Psychoneuroendocrinology,2002,27(1-2):171-180.
医学博士,中国首批国家注册心理督导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武汉市心理医院常务副院长,武汉市心理卫生研究所所长。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精神分析学组华中地区组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获得德国对外学术交流基金(DAAD)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及获得国家教委对外学术交流基金留学奥地利茵斯布鲁克(INNSBRUCK)大学。
免责声明
版权所有©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本内容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审定并提供,其观点并不反映优医迈或默沙东观点,此服务由优医迈与环球医学资讯授权共同提供。
如需转载,请前往用户反馈页面提交说明:https://www.uemeds.cn/personal/feedback
作者:施琪嘉,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武汉市心理医院常务副院长;林瑶;吴和鸣
编辑:环球医学资讯贾朝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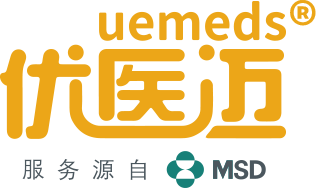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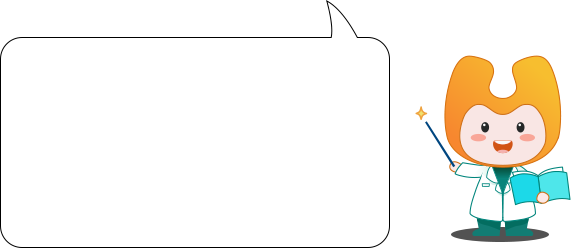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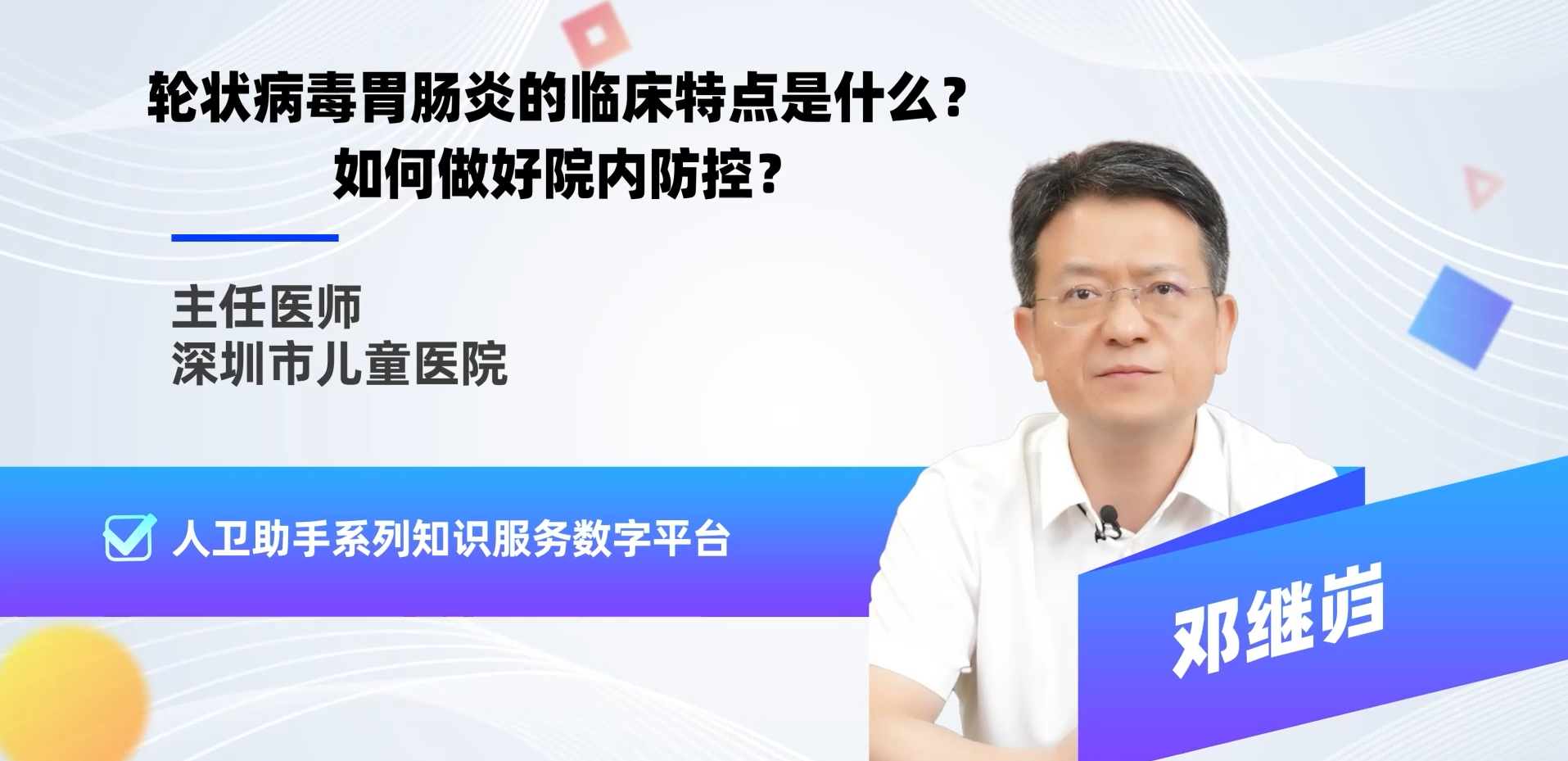
 Copyright © 2025 Merck & Co., Inc., Rahway, NJ, USA and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25 Merck & Co., Inc., Rahway, NJ, USA and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