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疗原则
癫痫的治疗既要遵循基本的治疗原则,又要做到个体化处理,这在女性癫痫患者中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癫痫的治疗原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正确的癫痫诊断及分型
正确的癫痫诊断和分型是治疗有效的重要前提。在治疗前应明确是否可诊断为癫痫、癫痫发作和癫痫(综合征)的类型、癫痫的病因、癫痫发作的诱发因素等。一般而言,有两次非诱发性癫痫发作(即可诊断癫痫)后开始治疗是合理的。如果发作间隔长于1年,或有明确的诱发因素(反射性发作、酒精、药物等),可以先观察随诊,避免各种诱因。通常情况下,首次非诱发性癫痫发作不需要治疗。不过,首次发作患者如果有脑电图明确异常(尤其是痫样放电)、影像学致痫病灶、神经功能障碍(如智障),则提示再次发作风险较大,在患者知情同意前提下可考虑开始治疗。在考虑治疗时,医生应与患者及家属充分交流,解释各种治疗方案的利与弊,最终决定权应交给患者和家属。应注意,患者的诊断并非一成不变,某些患者的癫痫及分型诊断在长期随诊中有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修正,尤其是在治疗效果不佳时。
(二)合理的治疗方案
癫痫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外科切除手术、神经调控治疗、生酮饮食治疗等方法。通常情况下,药物治疗是首选的治疗方法。对于某些诸如癫痫性脑病、抗体相关的边缘系统脑炎等导致的癫痫发作,针对特定病因治疗(如激素、丙种球蛋白等)可能要比单纯AEDs更有效。一旦开始服用药物,则应坚持长期足够疗程的治疗。一般情况下,在药物治疗完全控制发作2~5年后,可根据癫痫的病因、综合征类型、脑电图转归以及患者的实际情况来考虑是否需要尝试减停药物。同样,在减停药物前,医生应与患者及家属充分交流,解释减停药物的利与弊,最终应由患者和家属来决定是否尝试停药。应注意,最初的治疗方案并非一成不变,应根据患者的治疗反应来调整治疗方案。尤其在对药物治疗反应不好时,应考虑手术或其他治疗的可能。另外,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应教育患者保持健康规律的生活方式,避免发作的诱因,如睡眠不足、过度疲劳等。
(三)明确治疗目标
癫痫治疗的最终目标是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既要很好地控制发作,同时也应尽可能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在处理药物难治性患者时,不主张以任何代价来换取无发作的做法,应该在保证一定生活质量前提下平衡好发作控制和不良事件之间的关系。对于伴有躯体和精神心理障碍的患者,在控制癫痫发作的同时,还应进行相应的康复治疗,提高运动能力、心理素质、生活技能甚至工作能力,尽可能地鼓励患者参与家庭生活及社会活动。
二、治疗方法
目前,癫痫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外科手术、神经调控、生酮饮食等。
(一)药物治疗
AEDs治疗是癫痫治疗的最根本同时也常是首选治疗方法。目前,AEDs的选择主要依据癫痫发作类型、癫痫及癫痫综合征类型(表1)。选择药物不当,有可能出现发作不能控制甚至反而加重发作的可能(表1),要尽量避免。
注:VPA:丙戊酸钠;LTG:拉莫三嗪;CBZ:卡马西平;OXC:奥卡西平;LEV:左乙拉西坦;PB:苯巴比妥;TPM:托吡酯;GBP:加巴喷丁;PRB:普瑞巴林;CZP:氯硝西泮;ZNS:唑尼沙胺;PHT:苯妥英钠
此外,还应结合患者年龄、全身情况、治疗反应、耐受性及经济状况等综合考虑给予个体化的AEDs治疗。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癫痫患者都应遵循AEDs使用的重要原则:①尽量单药小剂量开始治疗,坚持长期规律治疗;②治疗中应注意监控并及时调整剂量,以达到最佳疗效和避免不良反应;③当某一药物使用足够剂量和时间后仍不能控制发作,和(或)有严重的毒副作用时,需考虑换药;④如果患者有多种发作类型,或者经用两种以上正规单药治疗证明无效后,可多药联合应用,但以两种AEDs联合为宜;⑤停药应根据癫痫类型及病因、既往发作和控制情况、颅内有无持久性病灶和EEG异常来决定,逐步停药的时间最好不少于1年。一旦选择了AEDs,通常65%的患者仅需单药治疗就能控制癫痫发作;35%单药治疗无效的患者中有10%的患者经两种AEDs联合治疗有效,对这些需要多药治疗的患者,应当尽量避免选择作用机制相同的AEDs联合使用(表2);还有25%不能控制的患者经两种以上的多种AEDs治疗后,仅有5%的患者治疗反应好,剩余20%的患者经过多种正规AEDs治疗,癫痫仍不能控制。
注:AEDs:抗癫痫药物;PB:苯巴比妥;PHT:苯妥英钠;CBZ:卡马西平;VPA:丙戊酸钠;ESM:乙琥胺;TPM:托吡酯;OXC:奥卡西平;LTG:拉莫三嗪;ZNS:唑尼沙胺;GBP:加巴喷丁;LEV:左乙拉西坦
约30%的癫痫患者对多种正规AEDs治疗都无反应,成为难治性癫痫。难治性癫痫的诊断也是临床工作中的一个难点,因为到目前为止都缺乏对难治性癫痫的确切定义。早期识别难治性癫痫,是合理选择治疗方法和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国内吴逊、沈鼎烈等在1998年对难治性癫痫的定义作了下述概括,即应用适当的一线AEDs正规治疗,药物的血中浓度在有效范围内,无严重的药物副反应,至少观察2年仍不能控制发作,频繁的癫痫发作每月4次以上,影响日常生活,同时并无进行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或占位性病变者。在2010年ILAE提出了难治性癫痫(refractory epilepsy)的最新统一定义,关于此定义的整体框架包含2个层面的意义。层面1提出了对药物治疗结局分类的纲要,包括确定疗效所必要的信息。治疗结局大体上可以分为“无发作”(seizure-free)、“治疗失败”(treatment failure)和“未知”(undetermined)3类。层面1是层面2的基础,层面2是在层面1的基础上提出了耐药性癫痫定义的核心,即应用正确选择且能耐受的2种AEDs(单药或联合用药),仍未能达到持续无发作。在该定义中,没有对难治性癫痫诊断前的药物治疗时间作出具体的规定,但是充分考虑了癫痫药物反应的波动性,能够减少对难治性癫痫的过度诊断和过度医疗。
在识别难治性癫痫时,也要注意考虑到其他的危险因素,如复杂部分性发作、婴儿痉挛及Lennox-Gastaut综合征等年龄依赖性癫痫性脑病;发作频繁,每天数次;出现过癫痫持续状态;有明确的病因,尤其是先天性代谢异常、颅内发育障碍及脑外伤等。临床上有些癫痫患者从诊断一开始就很有可能是难治性癫痫,而不是随病情演变发展而来。这些难治性癫痫主要包括:大田原综合征、婴儿痉挛症、Lennox-Gastaut综合征、Rasmussen综合征、Sturge-Weber综合征、持续性部分性癫痫、伴有海马硬化的颞叶内侧癫痫等特殊的癫痫综合征。难治性癫痫在儿童以Lennox-Gastaut综合征为代表,在成人以伴有海马硬化的颞叶癫痫最为常见。特殊病因引起的症状性癫痫常表现为药物难治性,如皮质发育不良性癫痫、糖尿病性癫痫、艾滋病性癫痫、重症颅脑外伤引起的外伤性癫痫等。
在我国,难治性癫痫患者也常常选择中医药治疗作为癫痫的辅助治疗。我国中医药对癫痫的记载最早追溯到《黄帝内经》,其中记载了癫痫的临床表现,且认识到癫痫与先天因素有关。明清医家对痫症的认识有了很大的飞跃,对痫症做了明确划分。王肯堂:“究其独言癫者,祖素问也;言癫痫、言癫狂者,祖灵枢也。要之癫狂痫,大相径庭非名殊而实一之谓也。”对于癫痫的治疗,元代朱震亨在《丹溪心法•痫》中提出“惊与痰宜吐,大率行痰为主,用连、南星、瓜萎、半夏,寻火寻痰,分多分少,治之无不愈者。分痰与热,热者,以凉药清其心;有痰者,必用吐药,吐后用东垣安神丸。大法宜吐,后用平肝之剂,青黛、柴胡、川芍之类,龙荟丸正宜服之。且如病,因惊而得,惊则神不守舍,舍空而痰聚也”。《临证指南医案.癫病》按语:“痫之实证,用五痫丸以攻风,控涎丸以劫痰,龙荟丸以泻火;虚者,当补助气血,调摄阴阳,养营汤、河车丸之类主之。”王清任继承脑为元神之府的观点,认为痫病的发生与元气虚,“不能上转于脑髓”,与脑髓瘀血有关,并创龙马自来丹、黄芪赤风汤主之。在古代医家对痫证的论述基础上,当代中医对癫痫有了更加完善的认识,总体认为,心、肝、脾、肾多个脏腑的功能失常是癫痫的内因,风、火、痰、瘀、惊诸邪扰乱神明是其外因,肝肾阴虚、阴虚则阳亢、阳亢则肝风内动、亢而热盛、热盛化火、火极生风、风火相助为患,另外脾虚失运、清气不升、浊气下降则痰涎内结、痰迷心窍、心血不遂而瘀、瘀则经络不通、痰阻血瘀上扰清窍,终致癫痫发作。多以调气豁痰、平肝熄风、清泻肝火、补益心脾、滋养肝肾、通络镇惊、宁心安神等法治之。全蝎、蜈蚣、柴胡、川芎、半夏、丹参、石菖蒲等都是常用的抗癫痫中药,这些药物的应用都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毒副作用相对较小。国家卫生部(现为国家卫生计生委)1993年制定了中药新药治疗痫症的临床指导原则,在治疗上按其病机以化痰、熄风、泻火等为治疗原则。例如,根据发病前有眩晕,头昏,胸闷,乏力,痰多,心情不悦,风痰上逆,气机不畅,发作呈多样性,或突然跌倒,神志不清,抽搐吐涎,舌质红,苔白腻,脉弦滑有力,为痰浊素盛,肝阳化风等表现,可辨证为风痰闭阻证,治以豁痰开窍,熄风定惊,代表方:定痫丸[《医学心悟》天麻、川贝、法夏、云苓、茯神、胆南星、石菖蒲、全蝎(去尾)、僵蚕、琥珀粉、灯芯草、陈皮、远志(去心)、丹参、麦冬、朱砂粉(水飞)、竹沥]。一些医家在临床中善于使用对药,比如石菖蒲配胆南星涤痰开窍;赭石配磁石镇惊安神;白矾、郁金、朱砂安神涤痰开郁;全蝎配蜈蚣熄风止痉;其中全蝎与蜈蚣配伍即为止痉散,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蕾等在癫痫患者及动物模型上均证实了止痉散治疗难治性癫痫的有效性,并发现止痉散可通过多途径干预多药耐药蛋白表达来调节癫痫耐药。
除了中药,针灸在癫痫治疗中的应用也很常见,应用体针取穴百会、人中、后溪、涌泉,耳针取穴神门、心、枕、肾,水针取穴大椎、风池、内关、足三里都有一定减轻癫痫发作的效果。女性癫痫除癫痫的共性表现外,尚有女性经、带、胎、产、乳的生理特点,与冲任督带密切相关,在治疗中要注意女性的生理病理特点,而中医的整体治疗观能在女性癫痫的治疗上发挥优势。月经期可有气血盈亏的变化,会使原先的气血不足,气血阻滞表现更为明显,此时要在调理气血上下功夫,气血不足者可以补气养血,比如当归补血汤,气血阻滞加重者可以使用四物汤等活血化瘀药物;带下对反映病邪的性质有所提示,色黄为热为实,带下赤白相间为肝经湿热,带下黏稠臭秽为湿热蕴毒。妊娠时注意女性阴阳气血的变化,注意顾护胃气和胎气,食物不可过于辛燥肥甘厚腻,药物勿用毒药,可酌加保胎作用的中药比如黄芩、砂仁、白术、杜仲等,并注意调护肝气,注意情志条畅,可用柴胡、紫苏梗、薄荷等药;分娩会出现气血的不足,如有产伤感染还会有湿热瘀毒,要注意辨证及选药的准确性;哺乳期要注意使用的中药勿伤及婴孩。由此可见,中医对癫痫的诊断和治疗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长期临床应用中也有一些疗效,在女性癫痫的治疗中也有一定的优势。当前,应用现代医学方法进行中医药治疗癫痫或者难治性癫痫的基础和临床研究都已经得出一些可喜的结论。但是,出于不同研究之间的研究方法不统一,以及实验设计欠完善,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医药治疗癫痫的系统评价结论还不乐观,中医药能否作为癫痫治疗的常规选择还没有答案,有待中医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外科手术
外科治疗是指通过切除致痫灶、阻断异常放电传导以及抑制致痫性放电等神经外科技术手段来控制癫痫发作的治疗方法。对于药物难治性癫痫患者可以考虑外科治疗的可能性。癫痫外科手术方式主要包括切除手术、姑息性手术及神经调控。对于癫痫灶和功能区定位明确的患者,可考虑切除手术治疗。切除手术方式包括病灶切除术、(多)脑叶切除术、半球切除术等。在致痫灶定位困难或存在多个致痫灶、致痫灶位于重要脑功能区时,可考虑行姑息性手术,目的在于减少或减轻发作。姑息性手术方式有胼胝体切开术、多处软膜下横行纤维离断术、低功率电凝热灼术等。
(三)神经调控
近些年来,神经调控治疗癫痫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临床应用的神经调控治疗包括:①迷走神经刺激术(vagusnervestimulation,VNS):也是常常被用来治疗难治性癫痫的方法,首先于1985年由Zabara提出,1988年美国Cyberonics公司成功地研制出迷走神经刺激装置,并应用于临床。VNS就是将迷走神经刺激器置入左侧锁骨下,刺激器电极固定于颈部迷走神经,刺激器不断发射电流,通过迷走神经传导到大脑,引起脑电活动及神经递质变化达到治疗癫痫的目的。通常,VNS治疗后癫痫发作会减少,程度会减轻,部分患者癫痫发作完全消失。另外,许多患者还反映他们的情绪得到了改善,记忆力也增强了。②经颅磁刺激术(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该技术作为一种非侵入性、无痛、无创的颅外刺激方法,通过对大脑皮质兴奋性的调控来抑制癫痫发作。据报道,能一定程度上减少难治性癫痫患者的癫痫发作。③脑深部电刺激术(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自1987年发展至今,已成为功能神经外科领域中的重要手术方法之一。近几年DBS在治疗难治性癫痫方面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尝试治疗的靶点有丘脑前核、中央中核和海马等,其中尤以丘脑前核效果最好,研究结果表明DBS在治疗难治性癫痫中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四)生酮饮食(ketogenic diet)
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酮食疗法也是难治性癫痫患者的一个选择,尤其在儿童癫痫患者中疗效确切,且有着较好的耐受性及安全性,但脂肪酸转运和氧化障碍为生酮饮食的禁忌证。生酮饮食是一个高脂、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其抗癫痫机制尚不清楚。目前生酮饮食的适应证主要包括儿童难治性癫痫、葡萄糖转运体Ⅰ缺陷症、丙酮酸脱氢酶缺乏症。近年来,在成人难治性癫痫甚至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中也逐渐发现其有一定的疗效。
在生酮饮食治疗前应对患者进行全面的临床和营养状况评价,完善相关检查,评估获益及风险。开始治疗初期应在院内观察,监测生命体征、血糖、血酮、尿酮等指标,有助于早期发现低血糖、高酮血症、酮症不足、消化道症状、困倦或嗜睡、癫痫发作增加等不良反应,并做及时处理。在随访期,应与家属保持较密切联系,定期评估患者营养状况、身高、体重,进行必要的实验室检查,酌情调整食物各成分的比例、热量和成分。如果治疗有效,通常可维持生酮饮食2~3年或更长时间。
参考文献
[1] Filipek PA, Richelme C, Kennedy DN, et al. The young adult human brain: An MRI-based morphometric analysis. Cerebral Cortex, 1994, 4(4): 344-360.
[2] Rose SA, Djukic A, Jankowski JJ, et al. Aspects of attention in Rettsyndrome. PediatrNeurol, 2016, 57: 22-28.
[3] Mertz LG, Christensen R, Vogel I, et al. Angelman syndrome in Denmark:birth incidence, genetic findings, and age at diagnosis. Am J Med Genet A, 2013, 161A(9): 2197-2203.
[4] Cowan LD. The epidemiology of the epilepsies in children.Ment Retard Dev Disabil Res Rev, 2002, 8(3): 171-181.
[5] Moshé SL, Perucca E, Ryvlin P, et al. Epilepsy: new advances. Lancet, 2015, 385(9971): 884-898.
[6] 中国抗癫痫协会.临床诊疗指南:癫痫病分册(2015修订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7] Fisher R, Acevedo C, Arzimanoglou A, et al. A practical clinical definition of epilepsy.Epilepsia, 2014, 55(4): 475-482.
[8] Commission of Classification and Terminology of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 Proposal for revised clinical and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classification of epileptic seizures.Epilepsia, 1981, 22(4): 489-501.
[9] Berg AT, Berkovic SF, Brodie MJ, et al. Revised terminology and concepts for organization of seizures and epilepsies: report of the ILAE Commission on Classification and Terminology, 2005-2009. Epilepsia, 2010, 51(4): 676-685.
[10] Commission on Classification and Terminology of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 Proposal for revised classification of epilepsies and epileptic syndromes.Epilepsia, 1989, 30(4): 389-399.
[11] Engel JJr, Pedley TA. Epilepsy: a Comprehensive Textbook. 2nd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William and Wilkins, 2008.
[12] Roger J, Bureau M, Dravet C, et al. Epileptic Syndromes in Infancy,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4th ed. Montrouge: John LibbeyEurotext, 2005.
[13] Kaplan PW, Fisher RS.Imitators of Epilepsy.2nd ed. New York: Demos, 2005.
[14]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NICE). The epilepsies: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the epilepsies i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care. 2012. NICE clinical guideline 137.
[15] Glauser T, Ben-Menachem E, Bourgeois B, et al. Updated ILAE evidence review of antiepileptic drug efficacy and effectiveness as initial monotherapy for epileptic seizures and syndromes. Epilepsia, 2013, 54(3): 551-563.
[16] Kwan P, Arzimanoglou A, Berg AT, et al. Definition of drug resistant epilepsy: consensus proposal by the ad hoc Task Force of the ILAE Commission on Therapeutic Strategies. Epilepsia, 2010, 51(6): 1069-1077.
[17] Kwan P, Schachter SC, Brodie MJ. Drug-resistant epilepsy. N Engl J Med, 2011, 365(10): 919-926.
[18] Chen L, Feng P, Li Y, et al. Influences of "spasmolytic powder" on pgp expression of Coriaria Lactone-kindling drug-resistant epileptic rat model. J Mol Neurosci, 2013, 51(1):1-8.
[19] Xiao F, Yan B, Chen L, et al. Review of the use of botanicals for epilepsy in complementary medical system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pilepsy Behav, 2015, 52(Pt B): 281-289.
[20] 谭启富.癫痫外科学. 2版.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21] Valentín A, GarcíaNavarrete E, Chelvarajah R, et al. Deep brain stimulation of the centromedian thalamic nucleus for the treatment of generalized and frontal epilepsies. Epilepsia, 2013, 54(10): 1823-1833.
[22] Cervenka MC, Henry B, Nathan J, et al. Worldwide dietary therapies for adults with epilepsy and other disorders. J Child Neurol, 2013, 28(8): 1034-1040.
[23] Kossoff EH, Wang HS. Dietary therapies for epilepsy. Biomed J, 2013, 36(1): 2-8.
北京市抗癫痫协会常务理事,协和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曾赴日本国立癫痫中心进行学习和研究。长期从事神经病学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以癫痫病学及脑电图学为主攻专业方向。已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特别擅长:癫痫诊治及癫痫的规范用药。
相关链接:
免责声明
版权所有©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本内容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审定并提供,其观点并不反映优医迈或默沙东观点,此服务由优医迈与环球医学资讯授权共同提供。
如需转载,请前往用户反馈页面提交说明:https://www.uemeds.cn/personal/feedback
作者:金丽日副主任,协和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编辑:环球医学资讯贾朝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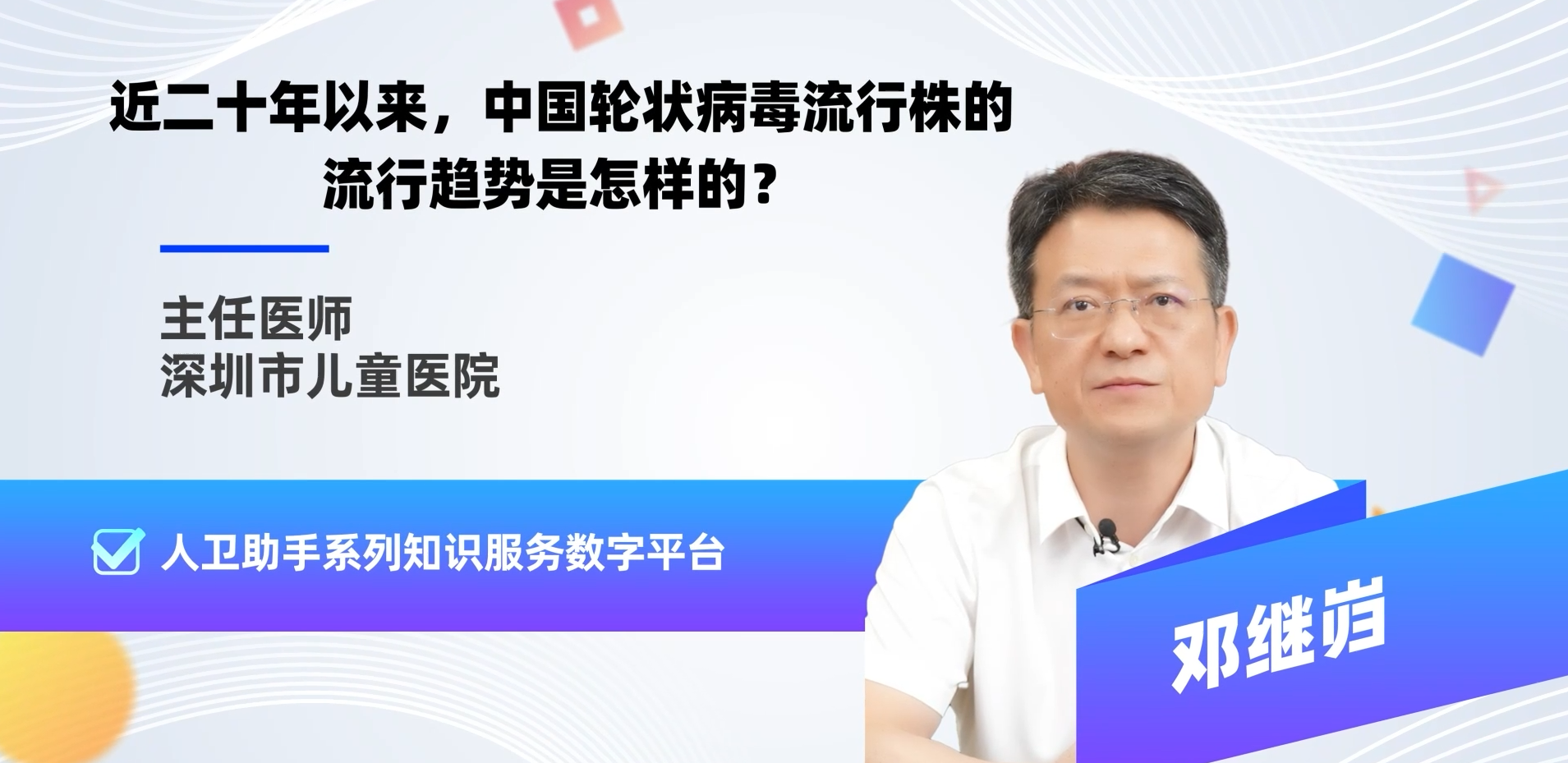
 Copyright © 2025 Merck & Co., Inc., Rahway, NJ, USA and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25 Merck & Co., Inc., Rahway, NJ, USA and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